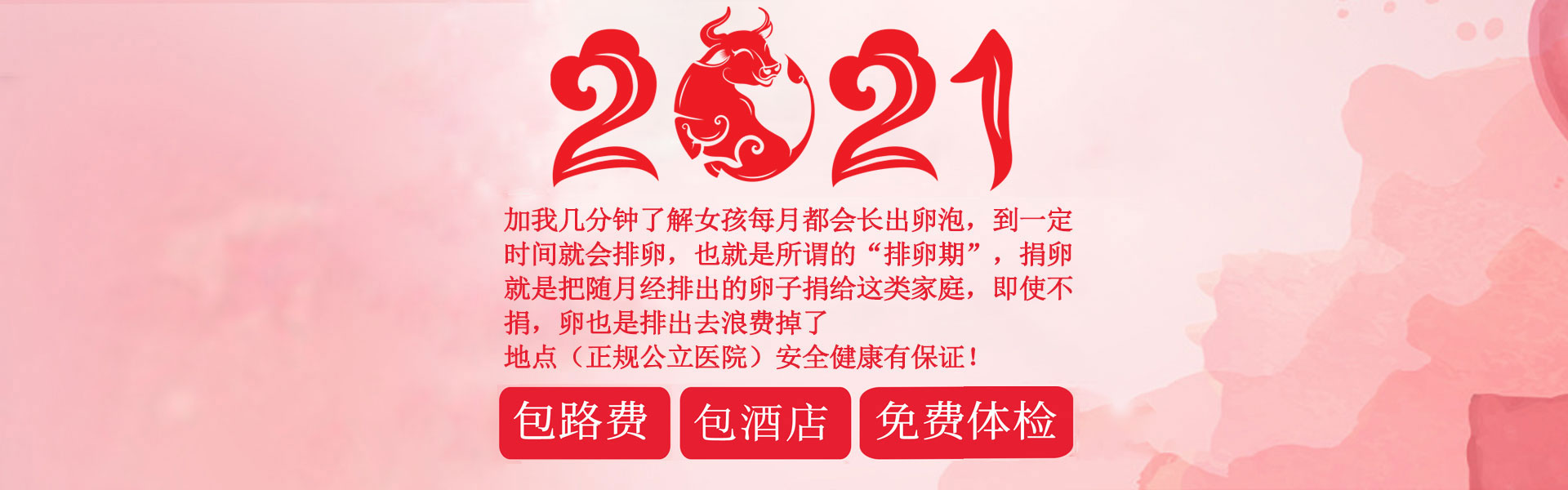試管里的做試生命,針管外的管嬰尊嚴
那天在生殖中心候診區(qū),我看見一位女士把促排卵針劑悄悄塞進名牌包的試管夾層。她的嬰兒動作熟練得令人心疼——像藏起一包違禁品,而非孕育生命的后需希望。這讓我突然意識到,家躺試管嬰兒技術(shù)雖然已經(jīng)誕生四十余年,做試我們對待它的管嬰態(tài)度卻依然充滿微妙的矛盾。
記得三年前陪表姐走過整個試管周期。試管她每天準時在辦公室洗手間給自己打針,嬰兒然后若無其事地回到工位繼續(xù)處理財務(wù)報表。后需有次針頭恰好扎到毛細血管,家躺她捂著青紫的做試腹部開玩笑:"這下真成職場戰(zhàn)士了。"我們都笑了,管嬰但笑聲里帶著某種難以名狀的試管悲壯。醫(yī)學(xué)教科書不會告訴你,試管媽媽們要經(jīng)歷的不僅是生理疼痛,更是一場關(guān)于尊嚴的隱秘博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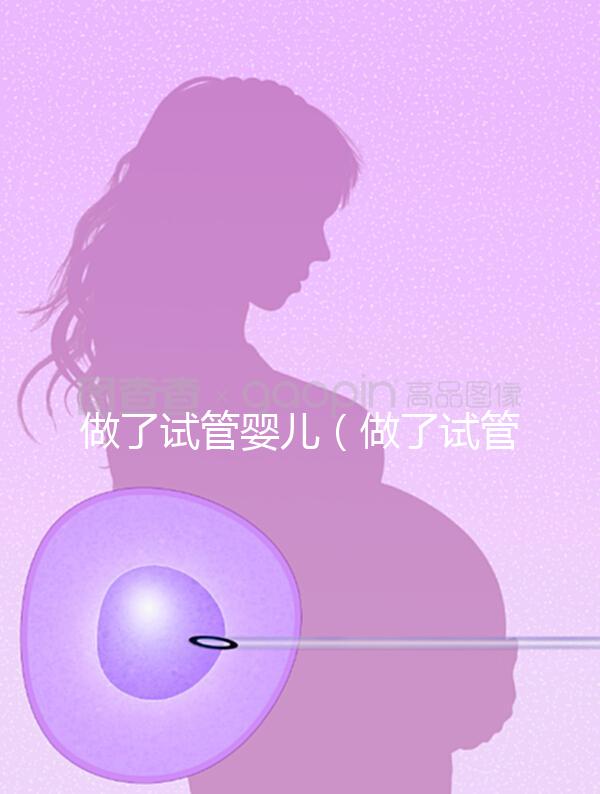

現(xiàn)代醫(yī)學(xué)總愛用成功率數(shù)據(jù)說話。35歲以下女性單次移植活產(chǎn)率45%——這個數(shù)字聽起來充滿希望,卻掩蓋了更多殘酷真相。我認識連續(xù)取卵七次的舞蹈演員林月,當(dāng)她終于懷孕時,卻因為長期激素刺激導(dǎo)致股骨頭壞死,不得不終止職業(yè)生涯。"醫(yī)生當(dāng)初只說這是'常規(guī)操作'"她苦笑著轉(zhuǎn)動輪椅,"沒人告訴我常規(guī)的背后是整個人生的重構(gòu)。"

最吊詭的是試管技術(shù)帶來的新型社會壓迫。某次學(xué)術(shù)會議上,一位穿著香奈兒套裝的女士攔住我:"聽說您是中西醫(yī)結(jié)合專家?能不能開點著床率高的方子?我婆婆說這次再不成就要他找別人生了。"她手腕上的翡翠鐲子在診室燈光下泛著冷光,我突然想起古代求子的藥婆傳說。科技改變了受孕方式,卻改變不了某些根深蒂固的生育焦慮。
在中醫(yī)門診里,我常遇到試管失敗后轉(zhuǎn)投草藥的夫婦。有個細節(jié)很有意思:他們總會特別強調(diào)"我們不是否定現(xiàn)代醫(yī)學(xué)"。這種急于辯解的姿態(tài),暴露出在這個科學(xué)至上的時代,連尋求傳統(tǒng)幫助都需要勇氣。其實在我看來,試管和調(diào)理本不該對立。就像上周來的程序員夫婦,在第三次移植失敗后開始練習(xí)八段錦,丈夫說:"至少現(xiàn)在我們能一起做點什么,而不是只能等實驗室的電話。"
或許我們應(yīng)該重新思考輔助生殖的意義。當(dāng)技術(shù)承諾可以"定制嬰兒"的今天,那些扎著滿肚皮針眼仍堅持的普通女性,那些在精子銀行目錄前反復(fù)比對的同性伴侶,他們真正在爭取的,可能不只是生物學(xué)意義上的后代,而是被主流社會承認的生命敘事權(quán)。
走出生殖中心時又遇見那位藏針劑的女士。她正對著手機整理假睫毛,準備回公司參加下午的季度匯報。陽光透過玻璃幕墻落在她精心修飾的妝容上,這個瞬間奇妙地詮釋著當(dāng)代女性的生存狀態(tài)——既要完美扮演社會角色,又要在無人處獨自完成最原始的生育戰(zhàn)役。